广州市电瓶车登记上牌数量突破560万辆,潮汐效应明显的地铁站出入口难以承载巨量车辆停放。
2.电动自行车乱停放问题已超越交通本身,成为一个社会综合治理问题,本质是城市稀缺资源分配的博弈问题。
3.为此,广州市政协委员刘继承建议增加地铁站周边的停车空间,加强执法管理,引导市民规范停车,并运用技术方法解决停车难题。
4.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交通研究所主任王雪认为,解决电瓶车问题是需要全社会形成共识,通过协商、妥协找到一个平衡点。
广州市政协委员、北京大成(广州)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继承(右)同南都记者走访大石地铁站出入口,调研电瓶车乱停放问题。
截至2024年底,广州市电瓶车登记上牌数量突破560万辆,且仍呈上涨趋势。潮汐效应明显的地铁站出入口,难以承载巨量车辆停放。针对“”停放乱象,记者调研了广州数十个地铁站、学校等公共场所后,邀请到广州市政协委员、北京大成(广州)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继承,以大石地铁站为对象联合调研并寻求解决办法。
从管理角度来看,地铁站出入口的“”停放管理涉及多个部门,管理方面存在“各扫门前雪”的情况,跨部门统筹协调对于减少人力投入、达到良好效果有积极意义。从现场观察来看,包括设置栅栏在内的物理隔离方式,相对于告示、指引等也更为有效。
在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交通研究所主任王雪看来,电瓶车问题已超越交通本身,成为一个社会综合治理问题。其本质是城市稀缺资源分配的博弈问题,在推行具体解决方案之前,全社会还须形成共识。
南都记者走访市内10个地铁站发现,多数地铁站的临停车位停满了电瓶车。无位可停的电瓶车在人行道、车行道等空间寻找“落脚之地”。
此外,电瓶车临停车位不足,跟规划滞后不无关系。走访调研过程中,南都记者看出不少地方临停车位的指示牌并未注明“电瓶车”,而是“共享自行车”。
在洛溪、南浦等地铁站,临停车位的指示牌清晰指明,此处系共享自行车的临停车位,而实际上停放的多是电瓶车。曾经,考验广州非机动车停车位供给的以共享自行车为主,高峰时期投放量超过80万辆,也一度“围堵”地铁站,给城市管理带来挑战。后来,电瓶车半路杀出,改变了原有“最后一公里”的交通出行格局。原本规划给共享自行车的近地铁站临停车位,迎来了保有量达560万之多的电瓶车。2月10日,广州市交通局计划再次调低共享自行车的投放量,降低至最高40万辆,给电瓶车腾出更多位置,希望以此缓解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停车难题。
南都记者此次走访的10个地铁站,也全部划设了临停车位。从现场情况去看,要在地铁站周边提供足够的临停车位并非易事,尤其是在空间资源本就紧张的中心城区。在燕岗地铁站B出入口前的小广场上,有一处长约10米的临停车位,能停下十余辆车,但这远远不能够满足现场的停车需求。临停车位停放了两排车,内排车辆被堵得严严实实,电瓶车沿着出入口两侧的人行道排开数百米。
记者调研了10个地铁站“”停放乱象后,邀请了广州市政协委员刘继承参与联合调研,寻找破局方法。2月13日14时,调研团在大石地铁站C出入口开始调研。出地铁站后,通道两侧树木下方系电瓶车的停放区,区内密集停满了电瓶车和自行车,若要挪动十分不便。部分车辆倒在地上,部分则显得锈迹斑斑,看似是久未挪动的“僵尸车”。
由于空间存在限制,电瓶车便沿人行通道朝更远处停,一眼望不见头。人行通道被占用,只留出狭窄的行走空间,偶有车辆停放在盲道上。出站后右拐,是“地铁大石(新光快速)”公交站。站台上也停放了几辆电瓶车。“此前在另外的地方没见过这样的一种情况,有点夸张。”一位来广州旅游的乘客向记者说道。现场,电瓶车还紧挨着人行道护栏,停放在非机动车道上。在更远处的商场广场台阶前,电瓶车紧挨着停放了一整排,阻拦了人行道进入广场的道路。
在大石地铁站A出入口,占道停车情况相对较好。出站后,除马路对面停有电瓶车,靠近地铁站出入口的一边并无电瓶车身影。一方面是带有角度的护栏,强制性阻拦了电瓶车靠近地铁站出入口。另一方面则是出站右拐处设有一处集中停放点,此处停满了电瓶车。但记者观察发现,该处墙面告示写有“严禁停放”的标识。因该处车位足够,整体的人行空间得到了保证。但记者也发现,电瓶车乱停乱放占用人行道和盲道的现象依然存在。
调研发现,张贴在地铁站出入口的“禁停告示”在停车的硬性需求下收效甚微。大石铁站也张贴有停放指引,但依然没办法避免乱停乱放发生。在记者此前调研的燕岗、同和等多个地铁站,电瓶车则公然停放在“禁停告示”指明的禁停区域,也有直接将告示遮挡住的行为。有负责电瓶车管理的地铁方面工作人员向记者直言“根本管不住”。
综合多处现场情况,记者发现,通过“物理隔离”,即通过栅栏或其他实体物件,明确将禁停区域隔离出来,或是有效管理车辆在禁停区域停放的方式。记者在人和、同和、燕岗等多个地铁站均有发现,即使停车空间十分紧张,乱停乱放突出,通过铁栅栏等物理方式强制性隔离出空间,也能有效阻止电瓶车的进入。
此外,地铁站出入口周边的物业权属复杂,这让停放管理工作的职责划分也变得复杂——涉及交警、交通、城管、街道、地铁等多个部门和单位。一些地铁站出入口无人管理指引停放,另一些地铁站则有专人从事此项管理工作,分别来自不同部门和单位。
在大石地铁站C出入口,地铁方面安排专人值守,工作内容单一,就是保障属于地铁方面的道路,尤其是确保消防通道不被占用。其他空间的停放问题,则不属于他们的管理范围。在调研过程中,来自街道安排的工作人员正在清理停放在非机动车道上的电瓶车。他们也清理了位于公交站台上的车辆,并在站台两侧围起了铁栅栏。不同的部门和单位负责各自范围的车辆停放,形成“各扫门前雪”的分工状态。
广州市政协委员、北京大成(广州)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继承在接受南都记者正常采访时表示,电瓶车乱停车、占道堵塞通道的现象有多方面原因,包括保有量与日俱增、停车配套设施不足、管理和执法难度大、市民规范意识尚不足、城市规划仍滞后等问题。
例如,在管理方面,地铁站周边的停车管理需地铁部门、属地街道、城管等部门共同协作,但真实的操作中常常出现管理空白,这需要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,形成合力;在规划方面,早期的城市规划没有充分预见到电瓶车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,导致现有道路和停车设施不足以满足实际需求。
刘继承认为,解决地铁站出入口电瓶车停放太多堵塞通道的问题,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措施,包括优化停车设施、加强执法管理、引导市民规范停车、加强宣传教育等。要增加地铁站周边的停车区域,包括利用空地、广场、桥下空间等设置电瓶车停放区;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,设置多层停车架,增加停车容量;引导市民将电瓶车停放在稍远但方便的停车区域。
此外,各街道和有关部门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,每天多次巡查地铁站出入口,及时清洗整理乱停放的电瓶车;街道联合交警、派出所、城管等部门,定期开展联合执法行动,对乱停放的电瓶车进行拖移和处罚。
刘继承还建议,运用技术方法解决地铁站周边的停车难题,包括在停车区域安装智能停车设备,如地磁感应、摄像头等,实时监测停车情况,及时有效地发现和处理乱停放行为;开发手机应用,方便市民查找附近的停车区域,引导市民规范停车;在地铁站出入口设置电子围栏,限制电瓶车进入禁停区域,一旦电瓶车进入禁停区域,系统自动发出警告。
刘继承和记者说,目前广州已有一些街道先行先试,通过增加停车空间、加大执法力度、引入志愿者力量等方式,某些特定的程度缓解了地铁站周边的停车乱象。
电动自行车的治理难题并非广州一城独有。截至2024年,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杭州、苏州等非流动人口超千万城市的电瓶车保有量都超过了500万辆,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治理难题。在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交通研究所主任王雪看来,电瓶车问题已远不只是交通问题本身,而已跃升成为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综合治理问题。
“多年来,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交通专家,包括政府部门都在讨论研究电瓶车的处理方法。”王雪认为,之所以多年难解,正是因为电瓶车已是一个社会综合治理问题,没有一个技术上的方案能像吃一剂猛药一样“药到病除”。
从社会综合治理方面出发,王雪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达成共识。“在超大城市,电瓶车所带来的治理问题归根结底是稀缺资源分配的利益博弈问题。”王雪解释道,每一个人在城市里的身份是多重的,既是行人,也或多或少驾驶乘坐机动车和非机动车。是人行空间让一些,还是机动车道让一些,分别让多少,这需要各方协商。
“只要全社会形成共识,治理的政策实施便没那么大的压力。”王雪认为,这也是媒体参与报道的意义,有助于共识的形成。她还提到,当前网络上市民对电瓶车的乱象发表了诸多意见建议,不乏带有情绪的声音。她认为,这至少表明市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,以及表达渠道的畅通性。若能得到回应,将有利于全社会共识的形成,政府部门大可客观平和地看待。
作为交通领域的研究专家,王雪长期关注电瓶车治理问题,也是电瓶车的使用者。她提出,应像管理汽车一样管理电瓶车,通过经济杠杆调节停放空间不均衡问题,有助于规范秩序的形成。例如,商事主体可先行在自有空间探索停车收费模式,既让电瓶车使用者在享用城市空间时像汽车一样付出对应成本,也让权属方在提供停车空间和管理服务时“有利可图”。
王雪表示,五年前她便提出了这一建议,但落地存在困难。“归根结底,还是回到前言,电瓶车的管理不只是技术问题,更是社会综合治理问题,一定要通过协商、妥协,找到一个平衡点,形成共识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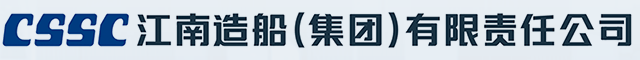

关注官方微信